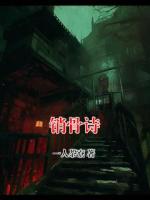《销骨诗》 第二章长兄为父,何来阋墙 在线阅读
刘长绫最近被喂补得火大,正愁一身力气没地方使。虽然贵为王爷,一人之下万人之上,可刘长绫在外征战与曲夜聚少离多,恩爱的次数也是越来越少,这让淮南王特别不满。
要是没有曲夜的劝导,刘长绫恐怕脑子一热真的打起自己人来了,大不了再跪牌位前边和哥哥认错呗。
没想到自己为国家和平作出了贡献的曲夜,被战功赫赫的淮南王以“亲一口给个甜头”为借口,尝了一夜。
刘长绫早上训练完士兵,回帅帐洗脸更衣。外面冰天雪地,洗脸水也十分冰冷他也不在乎。身在军营,本就比在京城和封地清苦些。
“王……王……爷……”
看着曲夜一副含羞带怯的模样,刘长绫马上精神起来了。
“你先歇着,大军正在开拔,你跟在后头。”
曲夜脸一红,不说自己一个大男人被这么照顾很别扭,他好歹也是武将出身啊……
派出的信鸽和送塘报的士兵至今杳无音讯,十五万大军在边境就和瞎子一样有家不能回。
之前为了保险起见,除了派出的一小队送塘报的士兵和四只信鸽,刘长绫另外往自己京城旧部和一向不和的京城顾家传了两只。
现在只有顾家回信,回的还是:王爷辛苦,万语千言不知从何说起,就不说了。——顾诗昂敬上。
自从看了这封信,淮南王刘长绫气得一天没吃好没睡好。
刘长绫作为主帅再次更换命令,旗手接到指令放倒帅旗,十五万大军穿着冬衣隐遁行踪开始弃装简行。大军向西行进,按照路线不过半月便可穿过河西走廊,直击匈奴个措手不及,着实是个好计策。
听闻路线改变的曲夜借了匹黑马就从队尾赶了过去,曲家以武见长,也就只有刘长绫把他当个纸片护着。
“王…”见刘长绫瞪眼,曲夜马上改口,“长…绫,不能…打匈奴。”
刘长绫自认为这个计策绝妙无比,还是细听曲夜的谏言,“为什么?”
“无诏…不得出兵…”
刘长绫用牙咬唇,右拳砸了一下左掌:该死的,若是兄长听信了那起子小人的谗言带兵……自己那些幕僚们恐怕还以为本王要……
虽然真的疼惜这次重创匈奴的机会,可若不是兄弟情分不能伤,恐怕刘长绫早就不管不顾地杀回王都了。
“吁——”
将士们看见前方软甲在身、披着毛披风的亲王勒马回头,尤其是那双久经沙场才能有的眼,锐利而深邃。
曲夜现在担心的是朝令夕改会使淮南王的威信下降。
“兄弟们!你们想不想你们的婆娘和儿子?”
淮南王刘长绫手底下的几个将军还没闹清楚发生了什么,身后乌压压一片士兵就大喊,“想!”
“已入寒冬,我们回家老婆孩子热炕头!”刘长绫的大喊猝不及防,举起兵符,“众军听令!整理队伍,回家!”
担心是多余的。曲夜把脸放在锦毛披风的阴影里,红着脸笑。
大军正在岔路口,东边是自己家右边是匈奴,也不用掉头,直接往东开拔大军就好。十五万人的军队黑压压一片,脚步比来时轻快许多。
“报——报——不足百里处,有…有大队人马往西北而来!”
刘长绫不想往下想,也不敢想,若真的是…他又怎能让曲夜因他身陷囹圄!
“王爷!”
他抬手制止手下的话头,腿夹马腹走在了队伍的最前方。
不多时,两军相距不过一舍,已能和家乡而来的军队摇摇相望。
“王爷!”
刘长绫面色凝重充耳不闻其他声音,自顾自地拿起曲夜的手把玩。
“王爷!”
刘长绫立于马上,话里带着少有的愠怒,“我是死了吗,这么给我叫魂。”
想劝谋反的人立马低头请罪,“卑职不敢。”
刘长绫知道大臣说的话必定比他听到的难听百倍,什么“居功自傲”、“功高震主”、“忤逆圣意”、“混淆视听”……
真的是一场豪赌。
终于,廿五日清晨,两军在弋房坡前对垒。
淮南王刘长绫手抓缰绳驾马在最前端,一副泰山崩于前而面不改色的模样。
僵持了半个时辰,一个一身黑貂毛披风、穿着干练的锦缎骑服的人踏马而来,气质华贵,举手投足之间散发着天子威严。
若不认识马上的人也无妨,便只看那人胯下之马,棕黑色的毛发浓密油亮,肌肉隐隐凸现,曲颈前伸,行、跃矫健而轻盈,不是帝王座驾凌风还能是何?
竟然是帝王刘长凛亲自带兵,果然是要御驾亲征吗!
哒哒的马蹄声使几十万人的沙场上瞬间安静,前排步兵自动给皇帝让开一条路。
淮南王刘长绫踏马缓缓迎上去,手里却暗暗将缰绳缠了两道,对着自己哥哥一脸淡漠疏离。
两人身上皆有兵刃,刘长凛腰间配有彰显皇帝仁德的剑,其弟刘长绫多年驰骋疆场,擅长长刀,使得是虎虎生风。
刘长凛左手拽住缰绳右手拿马鞭,看着弟弟显狼狈的胡渣和青黑的眼底皱眉,不知道在想什么。
刘长绫不像哥哥一样八风不动,被古井无波的眼睛看得紧张,拿长刀的手心也出了汗。若不是身后十五万士兵和曲夜,莫说是要他刘长绫一世英名,就是要项上人头,给自己兄长也是给得的。
腿夹马腹,宝马凌风通人意般驮着刘长凛就到了两军之间,逼得刘长绫胯下的战马不住后退。
——十日前
第一公子上表,求见皇帝陛下。
“朕千万个不信长绫有不臣之心,但有四成可能,是有人中军篡权或是蛊惑长绫,”皇帝刘长凛扔下大臣弹劾的折子,“顾郎同舍弟一向剑拔弩张,为何肯替他说公道话?”
帝王心如载舟之水,到底难以推测。
“草民……”
皇帝抬手,“免了。”自从听了顾诗昂的一句客套话,以后听大臣们的问安都感觉虚头巴脑的。
“陛下同王爷除了一奶同胞还是双生子,若是陛下尚有护弟之心,王爷更是比陛下多出万倍担心兄长。”
年轻的帝王打量殿上人,带着严肃的表情微微点头,“接着说。”
“陛下请看,此是王爷飞鸽传书。”
皇帝刘长凛腾地一下从龙椅上站了起来,胞弟一去塞外了无音讯,十五万大军一封信也不见带回,这是他亲眼见到的第四封塘报,前三封都不过是先前刘长绫安顿兵马时一些无关痛痒的信札。
“估计王爷投鼠忌器,才启用我给的信鸽。”
信上言辞恳切,详详细细,顾诗昂连他们的私信也拿了出来,只为消除帝王疑心。
“朕只存一丝好奇,长绫同卿家政见不一常针锋相对,如今看起来……”私交甚笃?
“国之存亡,大于私怨。”
字字铿锵,只因说话的是第一公子顾诗昂,七年前也曾献奇策立下功劳,他说话的分量可算一字千均。
事后,皇帝才从胞弟刘长绫那里看到他和顾公子的全部往来书信。只要出兵,不管大小战事,高贵如淮南王刘长绫皆向顾诗昂这个“纸上谈兵”的白身伏低作小,只求稳妥。
看着满纸“赠公子粉栗白藕羹”和“玄都蜜饼风味更佳”之类言论的皇帝疼了牙,这也太有损皇室威严了吧!
此刻那个有损威严的淮南王正和自己胞兄布兵对垒,几位将军及众军副将紧握缰绳,坐在马上屏息观望。
皇帝身后还有几位兵将,在几个呼吸之间随皇帝策马到刘长绫面前,若要以此对抗千军万马是玩笑,不过若是以谋反的罪名把淮南王处死倒也是名正言顺。
此时机,天时、地利、人和,无不具备!
皇帝依旧坐在马上注视着刘长绫,看不出是怒是悲。男人二十岁正是年轻时候,他却满脸严肃、不苟言笑,还总是老神在在,半句话也没有。
皇帝刘长凛没动,身为王爷的刘长绫就更不能动了。两个人大眼瞪小眼,也不知道眼神波动出个什么结果,就见黑貂披风后摆微微飘起,那人打马向西,缓缓走来。
刘长绫见不得兄长同父亲如出一辙的冰霜模样,耷拉着脑袋像个受气包。手中长刀不引人注意地转了个方向,将刀刃冲着他自己。
刘长凛绷着脸,眼中却满含笑意,“为何失期?”
刘长绫低头。
“杳无音信……”皇帝双眼眯起,笑容显得十分危险,分辨不出喜怒。
……再低头。
然后就是重重的几鞭子落在了淮南王身上。
两人身后众军哗然,当朝皇帝竟然如此羞辱战功赫赫的淮南王!还好只是当着王爷亲军和皇帝亲军的面,也算顾全王爷面子。但是王爷久坐帐军中,又为常胜帅将难免心高气傲,可惜……
那些凭空惋惜的将士们根本不知道,久征沙场的刘长绫不是普通的养尊处优的闲散王爷,少时常打鸟爬树、引架斗狗,没少吃过鞭笞的苦,以至于犯了什么事儿没叫爹爹兄长打两下就一天不自在。
加上大雪纷飞,厚厚的棉服抵挡了鞭子的力道,老实躲在军中的曲夜终于放下乱跳的心,策马匿到刘长绫身边,下马,躬身请罪,“臣…罪臣曲…夜,拜见…吾皇。”
刘长凛横了乖宝宝似的弟弟一眼,抬手示意身后士兵向前集结,同王爷亲兵排在一处。
不知道是谁迫不及待想让皇帝手足相残,搞错了形式也会错了意,竟让人弄来一辆囚车,十来尺的大车轱辘在弋房坡的土路上咣当直响。
刘长凛看见脸上变颜变色的胞弟很不解,回头见囚车,兀得面黑眉皱,寒气甚于塞野风雪逼入骨髓。